
哈雷是一个睿智而散淡的人。没见面之前,我零碎地读过他的一些诗作。2023年暑假,我在奥克兰与他有过多次见面,品茗之余,聊了许多文坛佚事、特别是诗歌创作方面的事情。他用诗歌纪录生活,几乎每天都要写作。这次集中阅读他的诗集《黑沙滩》,真是一次美的享受,一次难得的愉悦体验。在许多人看来,新西兰是诗意的国度,长白云的地方。也有人赞美说,新西兰像是人间天堂。而在哈雷眼中,天堂的模样不过如此。他的笔细致地定格、描绘和聚焦这一切,深情地讴歌这一切,充满着自然本真的内在力量。
自然与诗歌,恰似源与流的关系,源深则流长。自然与诗人,恰似泉水与汲水者的关系,弱水三千,诗人只取最契合心境的那一瓢。读哈雷的诗集《黑沙滩》,就像是在游览美丽的新西兰,我们跟随诗人清新而隽永的诗歌语言在纳迪岛、火山岛、胡里阿半岛、拱门岛等远离大陆的岛屿上感受南太平洋的海风;在克莱德小镇、海上教堂、皇后镇等镌刻着历史痕迹的老街区领略异国风情;在贝壳杉、草海桐、鸢尾花、蓝松鸦、早樱等新西兰的一草一木中体悟诗人的所思所想。哈雷的诗歌仿若一颗镶嵌在遥远而神秘的南太平洋岛屿上的明珠,吸收着新西兰自然风物的精华,闪烁着自然风景的光芒。哈雷在蓝天、椰风、海岸、波涛之间放牧思绪,为天地接生,吟唱自然的颂歌,他在与自然的精神互通、渗透、融合中实现人与自然高度契合的诗意境界。自然的风物、自然的颂歌,共同塑造一位信奉自然之力、崇敬自然之美的自然诗人——哈雷。
写自然,写山水,并非哈雷独创。但哈雷的诗不是一般的自然诗或山水诗,他的视野独特,将新西兰的生活经验巧妙地融入到中国诗歌的书写范式中。自然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体现为非对抗性的,即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从《诗经》开始,自然山水景物就是诗歌用来比兴的媒介物,是人物生活的依凭和背景,而非独立的审美对象。到了魏晋南北朝,以谢灵运、陶渊明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开始把自然景物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引入诗歌中,在自然之中探寻宇宙人生的哲理。唐宋时期,诗歌中自然与人的关系更为亲近,诗人们与自然交友,从自然中汲取灵感,达到一种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状态。正如林庚先生所言:“山水诗是继神话之后,在文学上大自然的又一次的人化。”自然山水是中国古代诗人们的精神家园,他们或借景抒怀、或移情于景、或物我不分、或浑然忘我,自然山水之于他们是能与之对话交流的平等关系,他们着意在诗歌中表现一种不加雕饰的、恬淡自足的自然之美,追求与自然共生的中和之境。与中国传统山水田园诗着意追求人化的自然不同的是,哈雷诗歌里的自然则更多地是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还原自然的本真面貌,并且在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中,寻求人的自然化。

例如,在《鸟岛》一诗中,哈雷以“云端的叶子,也有它们的栖息地/在风指向的地方”两句诗轻轻飘飘地开头,一下子把读者的目光牵引到茫茫大海中的鸟儿栖居的岛屿。“大海的辽阔与苍茫,足够装下黑暗豢养的光/却容不下人类肉体翻滚的欲火”。广阔无边,容纳万物的大海却无法容纳下人类翻腾不已、难以估量的欲火。这是由于自然与人本身的异质性,这也是人类永远无法凭借心中的私欲占有自然的原因。“它们来到这里,不是来征服世界的/也不是来证明自己的伟大”。鸟儿与人类截然不同,这群自然的精灵从不试图征服自然,也从不试图借助征服自然来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与伟大。“是庇护一个卵,并让它学会飞行/在冬天,它们开始成长,独立的翅膀飞跃数千里”。鸟儿来到世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繁衍,这种朴素的愿望完全遵循自然的运行规律。鸟儿在这里就是自然的化身,从它们身上诗人看到了自己。“我是一个翻看大海的人,但从没像它那样/‘挣脱自身,独立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里尔克在《预感》一诗中将旗帜在暴风雨中舒展而又跌回自身的幻觉作为一种预感,诗人自己好像也与风暴、大海融为一体。在《鸟岛》中哈雷虽然寻求与自然意象的契合,但是最终未能挣脱自身,我终于还只是我,我只能还是那个翻看大海的人,却成不了大海,也成不了风暴。这是诗人试图回归自然本真的人生状态的冒险之旅,即使它是在精神的想象层面上悄然发生的。

而在《告白》一诗中,哈雷虔诚地栖息在一片海岸上,希图将自我彻底融入自然风物之中,直至化为自然的一部分。“我将长隐长白云之乡/最后用诗句、骨灰和花草贴入土地/完成一个人的临终关怀/是必要的”“我因诗歌而转世来到这个世界/离世后/我会变成岸边一块草木/为自己歌唱”。哈雷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人生境界,是自然化的自我,是人与自然的神秘交感。面对身体与灵魂的矛盾,哈雷选择去往大自然寻求解决之道。《和稀少的人,交换脸上的微笑》中诗人有感于“世界在不断竞争中衰老/人性在相互争斗和仇恨中沉沦”,从而希望远离人群,去往一个“有连绵的海湾,还有持续春天的庭院,有步道/有停止在花草上的时间,突然造访的鸟群”的地方,这是一个远离现实人类世界的自然之地,一个人类灵魂的避难所。自然在这里不再是品德、品行的指代物,不再承担着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比德”责任,而是非人化的自然本身,只是凭借它原本的面目就足以净化诗人的心灵。“和稀少的人,交换脸上的微笑”,也就是和自然的、纯真的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的交往。
自然风物在哈雷的诗歌中除了具备疗愈功能之外,还具备一种类似宗教般净化的力量。在诗歌《空碗》中,“天就是具空碗,它清空了彩虹/包括时间。梦想/和高踞的神”,天被赋予了无穷广大的力量,“大海,不过是碗里的一滴水”,在如此广袤的天面前,“坐在太平洋黑礁石上/我像一个弃世者/又回到餐桌前。接过上天递来的空碗”。我置身于浩瀚无垠的天地之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震慑住了,我仿佛抵达了另一个纯洁、神圣的世界。这是一首纯粹的意识流动的诗,诗歌的最后一节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川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里的诗句“让灿烂的群星如亿万只脚/把我的肩头踩成祭坛/我像是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摒住了呼吸。”同样饱含暗示性的诗歌语言,节制而又浪漫的诗情,通过天空的自然意象寄托了诗人对永恒、纯粹、神圣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与向往。在这个自然与人类关系日渐疏远的现代社会,“人为自然立法”、“工具本体化”、“人定胜天”等思想观念极力宣扬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了对抗性,自然只是在充当人类社会的时尚装饰品。哈雷的诗歌则试图找回人与自然亲密友好的相处状态,重返自然的家园,找回人类的自然本性。
哈雷的诗歌清新纯净,唯美浪漫中又不失坚硬的内核,他将新西兰天堂的美好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他的诗歌像是璞玉,散发着柔润的光,又有着坚实的质地。他秉承着及物的写作态度,不凌空蹈虚,不矫揉造作,而是以浪漫而矜持的诗风,平缓而激荡的诗情,在新西兰的自然风物里,书写着人与自然的故事,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交融中追求人的自然化。(聂茂 凡哲汝)
【作者简介】
聂茂,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鉴定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鉴定专家,权威期刊《文学评论》外审专家,中国作家协会网络小说排行榜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台湾唐奖汉学奖评选委员会评委,湖南省新闻奖评委,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评委,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等。
凡哲汝,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师从聂茂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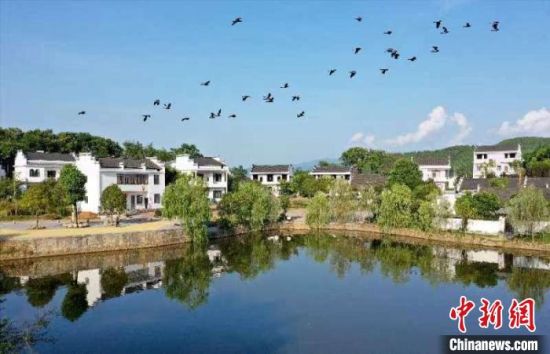







 多国演员张家界峰林秀杂技
多国演员张家界峰林秀杂技